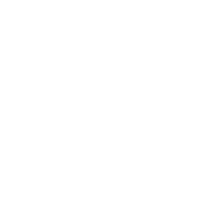这儿是十点人物志的名人采访栏目“向少数人提问”。我们将作为发问者,与不同行业、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聊一聊,从别人观念与经验中,找寻个体力量怎样应对复杂世界的答案。
明天是世界读书日,十点人物志专访到了近日饱受关注的”外卖员作家“王计兵。我们聊起,在这个时代,读书写作对普通人的意义是哪些?王计兵的答案是,“文学挽救了我的生命。”
专访、撰文|灯灯
十点人物志原创
今年春天,一首名为《赶时间的人》的小诗,忽然在微博上传播开来。
诗的作者叫王计兵,是广东苏州一名53岁的外卖员。
这天,一个客户留错了地址,王计兵白跑了两回,第三回才找到位置,累得满身大汗。客人接过外卖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骂:“你是怎样送外卖的?”王计兵刚想解释,订单超时的警告声却接二连三地响起。
回去的路上,王计兵写下这首《赶时间的人》,记录外卖员的生活常态:
从空气里逐出风
从风里逐出刀子
从腿骨里逐出火
从火里逐出水
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
只有一站和下一站
——节选自《赶时间的人》
诗火了,关注骤然而至。人们发觉,那位皮肤惨白、憨厚寡言的外卖员阿姨,早已默默地写作了近30年。
他的前半生做过许多活计,捞河沙、摆地摊、捡废铁,没有一项和文学有关。但他未曾中断过写作。这些用铅笔写在废纸盒和烟盒上的诗,曾获得过国际微诗比赛的银奖。
前不久,王计兵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选《赶时间的人》。十点人物志通过视频专访了王计兵,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,我们聊起,在这个时代,读书写作对普通人的意义是哪些?王计兵的答案是,“文学挽救了我的生命。”
渔家少年的文学梦
王计兵第一次倍感被文学挽救,是在19岁的时侯。
那一年,他追随一支建筑队去北京打工。建筑队里的其他人,大多是早已成家的中年人。男人们围在一起,话题离不开女性、兄弟、孩子。王计兵年龄最小,融不进她们的谈话,常常成为众人闲暇打牙祭的对象。
当时,北京流行一种街边书市。每晚下午放了工,工友们拉帮伙同地去景区饮酒,王计兵便一个人去书市蹭书看。书市上的书都是些二手旧书,以仙侠、言情小说居多,王计兵抓起哪本就看哪本。路灯昏暗,他读得如痴如醉,老总快卖完了才恋恋不舍地把书放下。
小小的旧书摊就像避风港,给这个性格外向、独自在异乡打拼的年青人带来了极大的开导,“从此我每晚干活有了目标——昨天那本书我还没看完呢,明天上班后一定要再去读一读。”
才能自由地阅读乡镇外卖小程序,对王计兵来说,是一种新奇而奢华的体验。
他在四川丰县的农村长大,家境贫苦,母亲早年间帮生产队运煤时乡镇外卖小程序,被相撞的煤车砸中,失去了劳动能力,很长一段时间里,全家人都靠父母磨腐竹生活。每到夜晚,家人都睡下了,妈妈便开始在庭院里推石磨。磨盘转动的声音,成了王计兵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屋内兄弟二人,王计兵排名老幺,打小可爱、寡言、学习成绩好。家里有一整面墙,贴满了他每学期赢来的奖章。由于凑不齐杂费,王计兵小学没念完就退学了,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户工,开始了到处飘泊的打工生涯。
在南京的建筑队干了一年,王计兵回到故乡,和妻子一起在漳河里捞沙。王计兵说,那是他前半生最苦的日子,“人长时间地曝晒在流水里捞沙,皮肤会显得厚实,石子随着流水磨蚀身体,像砂纸在打磨皮肤。三天出来,手和脚都往外渗血。那个疼让你晓得哪些叫十指连心。”
生活坚苦,读书再度成了王计兵的“止疼药”。每次去乡镇的集市,他都要买回去几蛇皮袋的旧书。
王计兵/图源受访者
书读得多了,他忍不住自己动笔写。第一篇刊载在刊物上的小小说,名叫《小车进村》,讲的是一辆停在村口的普通转租车,被村党员误以为是调查组领导的专车,引起了一系列乌龙的故事,略带些红色诙谐的嘲讽意味。
刊物寄回村里,惹出了不小的麻烦。邻里乡亲一眼便看出故事中的原型,有人甚至直接找到王计兵的母亲,威胁他,让他管好自己的孩子。
母亲和王计兵提起此事,王计兵却不以为意。处女作的发表令他信心倍增,他准备再写一处长篇小说,每晚不仅捞沙以外,其余时间都窝在一间小屋里,废寝忘食地写作。
为了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,王计兵彻底将自己化作了小说里的男主人公。
秋收的时侯,全村的人都在打麦场上繁忙,只有他站在打麦机下,体会麦粒滚落的诗意;冬天出河工,你们都在挖沟渠,他忽然跳上山坳读书;最夸张的一次,是他讲到主人公遭受丧亲之痛,自己也换上了一身黑色的鞋子和袜子,整日在村庄里闲逛。
村里渐渐有流言传出,说他精神不正常。披麻服丧的行为,更是羞辱了思想传统的女儿。总算有三天,当王计兵捞完沙,回到小屋时,发觉他饱含了无数心血的二十万字小说原稿不见了——父亲烧光了它们,只留下了一堆纸灰。
悄悄写作的30年
烧稿风波后,王计兵整整两个月没有和妻子说过一句话。他心灰意冷,那年冬天也因而而显得分外严寒、漫长。
感情的到来,冲散了他的失意。在那以后不久,王计兵碰巧在沂海边结交了现今的儿子郭依云。谈起父亲,王计兵的神情顿时显得明朗,脸下浮现出温柔的笑意。父亲比他小三岁,在王计兵心里,父亲天真,善良,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男孩,“她十分女儿气,非常容易满足,和她交往我没有压力。”
离婚前,父母找王计兵进行了一场长谈,劝他放下纸笔,之后塌实过日子。王计兵答应了。虽然心中仍有不解和委屈,但从小到大对母亲的习惯性服从,还是让他立下了不再写作的誓言。
但是,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,心底的那道水阀,一旦旋紧了,就很难再关上。
停笔了一段时间,王计兵又开始写作,每次写出了精彩的诗句,总想和男友分享。原本,母亲都会应和他,次数多了,也开始不耐烦。“有时侯你正兴高采烈地给她读呢,她拿个盆丢地上,你的兴致也‘唰’地一下,没了。”王计兵笑着说。
从母亲的角度看,二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,写作不能改善生活,是个无用之物。另一方面,“她认为一个女人三天到晚在那儿埋头想事情,会显得多愁善感,优柔寡断,没有女人气魄。”
年青的王计兵和母亲/图源受访者
王计兵珍惜母亲的体会,不愿做她不喜欢的事,自此不再当着母亲的面读书写作,就连买了新书,也会把封套撕开,在地上搓一搓,滚一滚,撒上灰尘,佯装成捡来的二手书再带回去。
为了讨生活,夫妇俩东奔西走,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。她们去山西开翻斗车,在芜湖摆地摊,最困窘的时侯,全靠拾荒维系生活。
生活的苦难,成了王计兵创作的活水。节日坐列车返乡,坐在背对行驶方向的座位上,他形容自己,“仿佛生活的一次退款/一个不被异乡接收的中年人”;
年近半百,生活仍然摇摇欲坠,他慨叹,“就像一条夏日的河/开始覆盖一层薄冰/只须要一块石头或则半块板砖/轻轻一抛/就足以将平淡打破”;
外出打工回去,女儿看他的目光显得陌生,转头告诉妻子,“妈,哪个人回去了”,他认为艰辛,写下“一年未见/母亲还是我的孩子/老婆还是我的老公/只有我/从父亲弄成了农户工/从农户工弄成了那种人”。
这是一场经年累月的、不为人知的创作。为了不让母亲发现,王计兵每晚揣着一根铅笔出门,灵感来了,就写在随手捡来的烟盒和纸盒上,卖废铁时再一并卖掉。
最初,王计兵并没有作诗的意识,他的写作体裁更接近诗歌。成为作家,纯属意外。
2005年,他和女友结束半世流离的生活,在苏州开了一家小卖部。不久后,店里添置了一台笔记本。那段时间很流行写QQ日志,王计兵便每晚趁父亲还没睡醒,先去店里,把前三天写在废纸上的文章,偷偷记录在QQ空间里。他打字慢,假如把每篇文章都打出来,从早到晚都打不完,他只能留下最精华的句子,其余的都删除。
王计兵在看店时看书/图源受访者
日志发表后,一位热心的陌生网友给他留言,夸他的诗写得好,又给他推荐散文峰会,约请他一起玩。王计兵豁然大悟,原先这就是散文。但他仍执拗地守着对母亲的承诺,也保护着母亲的心情,不投稿,不谈论写作,虽然文学已经和他的生命密不可分。
一个外卖员的诗
2018年夏季,王计兵开始在苏州送外卖。小卖部下降的生意,和儿子们昂贵的杂费,让他急切地须要找一份副业提高收入。
骑着电动车,游走在城市的大道小巷,句子就在这种赶车的间隙中积聚。
王计兵在送外卖/图源受访者
他写自己去寺院送外卖的奇思妙想,“时间在催/我还有许多单子须要及时配送/此刻,我才是大士/面对诸多的许愿人”;
记录被客户挖苦的复杂心情,“我遭遇的白眼/像白云一样多/赔出的笑脸/像星星一样闪耀”;
也为和他一样的农户工群体发出悲鸣,“原谅我们争分夺秒/如同宽恕浩浩荡荡的蚂蚁/在大地的裂纹搬运着粮食和水。”
有媒体评价王计兵,“如同一个来自民间的苦吟作家,记录下劳动者的狼狈和自尊,这种句子是来自劳动现场的民歌。”
王计兵直言,送外卖对他的写作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,“以前我写东西会更自我一点,总身陷自己的情绪,送外卖然后,我忽然发觉世界不是我想的那种样子。过去我是从窗口看世界,如今我还能站在屋顶上,全方位地去观察这个世界。”
2019年,王计兵一首名为《白纸黑字》的诗,获得了国际微诗比赛的银奖。他去云南领奖,事后又用那笔奖金给儿子买了一件数千元的大衣——这也是母亲最豪华的一件大衣。王计兵向她坦承,自己未曾舍弃过写作的事实,总算彻底获得了父亲的理解。
王计兵的写作才气被听到,诗作获得业界认可,母亲是最沮丧的那种人。有一次,王计兵回去看望父亲,接到了当地作协打来的电话。王计兵告诉母亲,自己又开始写作了,妈妈沉默了很久,说,“我耽误了你那么多年。”
母亲的话像一记重锤,在王计兵的心中狠击了一下。前几年,父母早逝了。访谈中提起母亲,王计兵数次抽泣,一阵长久的沉默后,他用右手揩去脸颊的泪。
时隔多年,王计兵已经放下了对于当初妈妈烧稿的成见,“我当时那个创作状态显著是不正常的,家人都害怕这个小孩写书写成神经病了,这一辈子就完了”,但他能感遭到,母亲一生都背着沉重的包袱,“他会指责自己,责备自己,到生命的最后,也没能放下这个包袱。”
2020年,父亲也过世了。那位勤奋、节俭、隐忍的女人,为家庭奉献了一生,临终前仍在吩咐儿孙,丧礼中的空纸盒和空杯子,一定要及时收纳,由于丧礼过后,第二天必然有人上门回收。
双亲的陆续辞世,让王计兵深陷了巨大的痛楚,只有一遍满地作诗能表达他的遗憾和想念,也为母亲王丙现、母亲包成珍这两位最平凡的奶奶,留下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痕迹。
王计兵和家人在一起/图源受访者
离开的人早已远走,留出来的人,生活仍要继续。在一首名为《春天的车轮》的诗里,王计兵这样写:
假如,真的有另一个人间
母亲妻子,请大家
掉下两朵花瓣给我看吧
给我,一个制动的理由和一个
可以痛哭失声的夜晚
——节选自《春天的车轮》
文学挽救了我
年初,王计兵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选,《赶时间的人》。
聊起家人的反应,他笑得停不出来,“可以说是在我们家掀起了一波生活的高潮。”拿到书的第三天,父亲就向所有亲朋好友宣布了这个好消息。这天,王计兵照常送外卖,“我晚上出门的时侯,她就开始打电话,到我早上回去,她还在打电话。说的内容都差不多,但人早已换了几拨了。”
王计兵的长诗《赶时间的人》
相比父亲的激动,王计兵则显著淡然得多。过了半生苦日子,这个53岁的中年女人不再幻想着改变命运。对于成名这件事,他的心情很平淡,“我不发光,我就是沙滩上的一粒沙,正好被一束光照到而已。不管有没有被光照到,你仍然是沙滩上的那粒沙。”
在王计兵心里,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新书出版,媒体专访和活动邀约数不胜数,他一边感激人们的善意,一边也为自己持续增长的外卖员等级苦恼。他以前的等级是8级蜂鸟,近来掉回5级,相当于从黄金弄成了最普通的青铜,派单量和客总价就会相应降低。
外界的瞩目和赞誉,王计兵通通看作是一场梦境,“摆正自己的位置,该如何生活就如何生活。”有时侯,他也会想,公众喜欢他的诗,是不是有关心和同情的成份?“其实并不是你写得有多好,只是你们据说一个外卖员在写歌,感觉好辛苦,对你更宽容而已。”
至于现实层面,王计兵并非不盼望通过写作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,把自己和家人从每晚五点半早起、晚上十一点半休息的辛劳状态里解脱下来。只是,他认为这不是就能强求的事情,“现阶段不要把过多心思置于前面,还是要把店里的货物摆好,过期的挑出来,有灰的擦干净。”
物质之外,文学带给他的东西已然足够多。王计兵将自己称作农田里匍匐着的一株动物,而文学就是插在地上的竹竿,“文学支撑着我把生命立上去,让我活得更健康,更向下”,每一次写作如同照一次穿衣镜,是他对自我的一次对话和考量,会不断提醒他修正自己的过错,要做一个好人。
好多年前,曾有人问过王计兵,写作又不能改善生活,你为何这么喜欢它?王计兵笑了笑,回答,“反正我是寸草不生的一片空地,为什么不能让它飘一场大雨?”
未来,王计兵说自己就会继续写下去。他希望能将一生中美象深刻的事和盘托出,若干年后,后人能从他的作品里,找到他生命的线索。
王计兵觉得,再平凡的生命,也有书写和记录的价值,就像他在诗里写的那样:“我也有自己独立的国度/我险峻的瘦骨/就是我巍峨的山川/我沸腾的血/就是我奔流不息的江河。”
点个“在看”,再平凡的生命,也有书写和记录的价值
免责声明:部分文章信息来源于网络以及网友投稿,本站只负责对文章进行整理、排版、编辑,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,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,如本站文章和转稿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作者在及时联系本站,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。